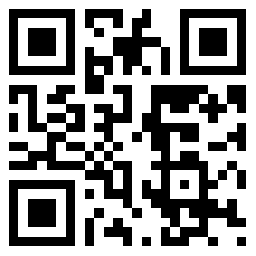近日偶翻史书,细读王安石改革之《青苗法》,确有几点想法。众所周知,古今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是政府所必须履行的职责。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职责是以政府赈灾、免赋、平抑粮价等形式来实施的。汉代创设常平仓,丰产则买,歉收则卖,平抑粮价;隋代设义仓,丰年征粮积储,荒年放赈济困,都曾起到很好的济困助贫作用。宋初在各地设常平仓与惠民仓,以调剂民食。虽然各地收效不一,但也体现了封建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应起的作用。王安石反其道而行之,将常平仓与惠民仓的钱谷挪作青苗本钱,放贷取息。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主要理由是政府将青苗钱贷给贫民,使之免遭富有之家的高利贷盘剥,解决其生活与生产问题。他曾说:“昔之贫者举息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政府半年收取二分息比之富有之家的高利贷要低些,多少可以减轻贫民的负担。可以看出,《青苗法》的出台和实施的本意是放水养鱼,恩泽贫民,但在实施当中却成了统治者剥夺财产的工具。
首先,从制度设计上分析,不难发现青苗法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不是济困助贫。欧阳修说:“但见宫中放债,每钱一百分要二十分利尔。是以申告虽烦,而莫能谕也。臣亦以谓等是取利。不许取三分而许取二分,此孟子所谓以五十步笑百步者。”(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奏议集》卷114《言青苗第一札子》)确实,青苗法除了把民间高利贷收入转化为国家高利贷收入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外,是不可能解决贫苦农民的生活与生产问题的。
同时,青苗法的实行还使政府蜕变为放贷取息的高利贷者。虽然,其名义利率要低于民间高利贷,由于政府具有更大的强制力,执行不当其危害程度甚至比民间高利率更大。韩琦曰:“故自敕下以来,一路州县上下惶惑,皆谓若不抑散,上户不愿请领,只据近下等第与无业客户愿请者支偯,则实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全宋文》卷846韩琦:《乞罢青苗及诸路提举官奏》)司马光亦说:“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 (《宋史》卷176《食货上四》)贫苦农民若无力还贷,青苗钱就无法周转,难以为继;如果政府强制催纳,必酿成社会动乱。
其次,强制抑配不利于抑制富人盘剥。如果说,青苗法的本意在于济困助贫,防止富有之家乘穷困人的急需而增加利息,青苗钱的放贷对象就应以贫困农户为主,且不许抑配,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富有之家原先就以高利贷盘剥贫苦农民,富有人的家资自然不需要贷钱,更不愿意偿付高息。王安石之所以将青苗钱抑配给乡村上等户有物业者,显然不是要济困助贫,而是要劫民户之富以济国家财政之贫。他曾对宋神宗说:“抑配青苗钱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户偯十五贯钱,又必令出二分息,则一户所赔止三贯钱,因以广常储蓄以待百姓凶荒,则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未为不善!况又不合抑配,有何所害,而上烦圣心过滤。”(《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8《青苗法上》)。由于贫苦农民无力还贷,青苗钱若放贷给贫苦农户,不但贷款风险大,收益更难以保证。反之,若将青苗钱抑配给乡村上等有物业者,既无放贷风险,又可以分割其部分利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记得在中学课本上的王安石变法是作为正面教材宣讲的,从史书上细读这部变法史,却感叹封建统治者为了搜刮民脂民膏而采取至极的办法。为了争夺天下,强行征兵于百姓;为了建造豪华宫殿,强征民夫于百姓;为了维持统治地位,强征赋税于百姓。老百姓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以《青苗法》剥削已经在生死边缘的老百姓。
一部中国历史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唤醒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短短的六十几年便将一个积贫积穷屡遭外国凌辱的国家,建设成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富强国家。取消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税,不但耕者有其田,而且耕田还有惠农补贴,农民不但享有老年保险和医疗保险,低收入群体还有最低生活保障。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确立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更是将全面提高相对贫困人群生活提到工作的首要任务。从中央到地方,都派出精干力量组成扶贫工作组,安排专项资金,驻村入户精准帮扶每一位贫困人口,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能幸福地生活,幸福地创造历史,改变历史。
历史在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相互帮扶、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才是历史的要求,才是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